






Articles and postings are about family matters, issues regarding Boston's Chinatown, and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rt,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will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discussions.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will be used.家事、同胞事、社區事,事事關心。藝人、文學人、政治人,人人著意。中英並用。

移民海外,人地兩生疏,每每到了中秋節前後,必定會令人有各種各樣的想法,究竟是天氣還是景物使然,引起的這些蕭涼悲愁的感覺,你我都會有不一樣的情懷。歷代詩人詞家曾寫過不少關於秋日的詩文,大多是一片哀傷淒涼,寸寸愁懷,隨手牽來的有辛棄疾的《醜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箇秋!
單看看這『愁』字,不是包含著一個『秋』字嗎?但在下面亦有個『心』字,光是這一點已經令人有不少的胡思亂想了,與其是說,人的心境隨著季節的轉變而增添了不少愁的滋味,不如說這個『愁』字總是離不開那個『心』字,更來得貼切。若然是內心帶著愁意,不管是到了那個季節,愁的滋味總是揮不去的。但是,如心境開朗,金華秋實,秋天正是收獲的季節,這裡華埠的團體,不是每年都在這時間組織摘蘋果、賞楓葉的活動嗎,『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這應是想心樂事,很多長者也參加。
秋高氣爽,除了遠足郊遊外,亦是進補的時刻。正所謂『秋風起、三蛇肥』,廣東人有吃蛇的偏愛,但是香港人在秋天,則是吃天天空運抵港的洋澄湖大閘蟹,配合數兩花雕酒或一杯加飯酒,是食客所追求的享受。不過,在波士頓三蛇與大閘蟹均欠奉,而中、老年人唯一可做的就是,煲一些廣東老火湯,如冬蟲夏草炖老鴨或沙參麥冬瘦肉湯,這些湯料都可在唐人街買到。《飲膳正要》言﹕秋氣燥,宜食麻以潤其燥。而喝有益健康的湯水,亦是生津潤燥的良方,況且,與親朋戚友一起品嘗得一碗好湯,不就是猶勝於身處江南嗎?
其實,無論生活在那裡,都會面對著種種的困難或不便,這要看看自己的心境,若能是身心安泰,對事情看開一點,樂觀一些,就能視波士頓唐人街為第二故鄉,滿載著溫暖與馨香。10/25/2006寫

蘇軾的好朋友王定國,擁有一歌女名叫柔奴,她家世世代代都住在京師,後來王定國官遷嶺南,柔奴亦同往,多年後才隨王定國返回京城。蘇軾在拜訪王定國時,再見到柔奴,便問她﹕「嶺南的風土應該不好吧﹖」怎料柔奴卻答道﹕「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軾聽後,心有所感,遂填詞一首,這首詞是這樣﹕「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在蘇軾的眼中看來,偏遠的嶺南不會是一個好地方,但柔奴卻能像生活在京城故鄉一樣,處之安然。從嶺南歸來的柔奴,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輕,笑容彷彿帶著嶺南梅花的馨香,這便是隨遇而安,並且是心靈之安的結果了。倘若柔奴到了嶺南,感覺自己身處異鄉,對那裡的環境處處不適應,當她萬里歸來之後,恐怕就不會是「年愈少」的笑容,也可能帶著漂泊的蒼傷,而不是嶺南的梅香了。
引述上面在網上看到的故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叫人『隨遇而安』,隨遇就是順隨境遇,但舊版《詞海》則寫成『隨寓而安』,而寓則有居所的意思,對僑居海外的群族,更加有另一深層的意義了。常常聽到一些新移民抱怨,說不能再在波士頓繼續呆下去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除了語言、生活習慣及經濟的原因外,必定有很多無法解決的疑難,才會有萌生離去的念頭。不過,若能好像蘇軾詞中所描述的柔奴一樣,能隨寓而安,波城華埠不就是好如家鄉般,有著嶺南梅花的芳香。境遇是一個問題,克服內心的障礙及疑慮,會是很困難,但仍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文革前,巴金由於高據權位,亦主持過一些批鬥大會,在長官意志下,做過有違良知的事情。但在革命洪流的沖擊下,亦關進牛棚,後得娘娘開恩,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帶帽子,可做翻譯,不能寫作。對曾被他落井下石的人,表示懺悔過,自己也受過苦,在感謝黨對他的寬大之餘,寫過歌功頌德的文章,這是文人的悲哀。一個弱質的文化人,在專權下,更感到無力。故在他還有幾分氣力和崇高的社會地位之際,倡議建現代文學館及文革博物館。
在黨的關懷下,兩者他得其一,現代文學館終在1999年建成,而文革博物館就不必多提了。其實,文革博物館早已建成,地點可在紀念堂原址,展品可以保留,只待換個招牌便可。
巴金在“第二次的解放”後,恢復寫作,在1978年開始,一共在香港大公報寫了150篇“隨想錄”。同時,亦在香港文匯報寫“創作回憶錄”,到1980年,共寫了11篇。在1981年,巴金停止向大公報供稿,抗議稿子多處被刪除,憤而擱筆。大公、文匯是香港左派愛國機關報紙,言論緊跟中央,巴金不可不知,對刪稿一事,又何須動怒容呢!不錯,在英殖民地統治下的香港,有較大的言論空間,但在無限忠誠的思想框架下,這些辦報人早已喪失獨立思考的人格,把天賦言論自由的人權,拱手向長官奉獻了。
巴金對八九民運不發一言。同年十一月,在家中親自接過朱榕基送來的老松盆景壽禮。一位85歲的老人,曾為民主而寫、為自由而歌,對著年青人在廣場為民主擾攘多月,終以流血收場,能不動情?面對廣大人民的社會訴求,是基於健康或政治的理由,令他默不作聲,還是在無聲抗議呢?筆者一直希望是後者,但願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往者已矣!對這位“文學巨匠”、 “人民作家”苛責之餘,還是帶著崇敬之心,願他在天之靈,仍會為自由、民主與志同道合的鬥士一起隨想!10/28/2005寫

“我愛月夜,但我也愛星天。從前在家鄉七、八月的夜晚,在庭園裡納涼的時候,我最愛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的繁星。望著星天,我就會忘記一切,彷彿回到了母親的懷裡似的。”讀書的時候,對巴金有點兒著迷,在香港就看過不少他的作品,這是巴金在1927年所寫的“繁星”。看來,這裡所說的“母親”,不會是指“祖國”或 “黨”吧!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想他必不會有這份“親情”!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對於他的筆名,一直有這樣的兩個說法﹕巴金這個名是取自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及克魯泡特金兩個名字中,各取首尾兩字而來。另外一說是,其筆名乃取自在法國的一個中國朋友巴恩波的巴字,及另一位朋友在他譯畢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建議他用金字合成的。在1929年完成了他的處女作中編小說“滅亡”後,便起用巴金這個筆名。
巴金一直活了101歲,最近(2005年)才去世。比起老舍、胡風不知多活了多少個寒暑。老舍在文革被批鬥後,投湖自盡,浩節高風,可昭日月。胡風坐牢至風燭殘年,崢崢傲骨,少活一些,亦無愧於父母、人群及讀者。以巴金自己所言,長壽是一種痛苦、懲罰,所以他要求安樂死。家人捨不得他,而沒有同意。不過,老舍、胡風可憾就連選擇這個權力都沒有。
長久以來,巴金面向社會低層,緊守著崗位意識,用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手執鋼筆,向著強權壓逼、社會腐惡衝刺。但到了新政權成立後,就脫離本位,走進廣場的廟堂,依杖權勢,在某種形勢下,反與民間權利抗衡,可以說,這是對自己的理想、作品及讀者的一種叛逆。
在1984年,這位80歲的老人,歡歡喜喜地到香港,接受中文大學頒發他榮譽文學博士。在1989年的春天,完成了“懷念振鐸”一文後,就不能再寫下去了。從1999年開始,巴金一直住在上海華東醫院,神智是清醒的,但有口難言,不能活動,思想不能表達。在死前,還掛著一大堆空銜及虛名,如政協副主席、作協主席、收獲雜誌主編。對老人家來說,這是社會給予他的一份可貴的尊榮及報酬。人們會問,這些組織的作用又會是什麼呢?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Bs9I41i7D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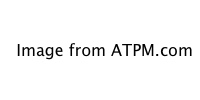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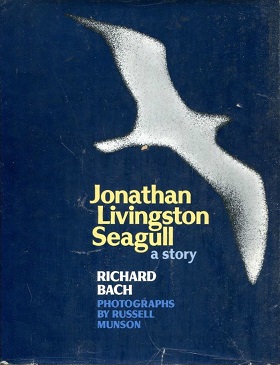







人間淨土 (下)
佛教所提出的經濟學理論,是與現今社會流行的物慾主義截然相反的。物質主義的經濟學就是不擇手段,運用一切資源,去令人們膨漲的慾望飽足,而得到快樂的滿足。而佛教的本義是淨化人格,以慈悲憫人的心,去善待一切生命,而推廣到愛護一草一木,同樣給予平等的尊重,以簡樸清淡的生活態度,去抵消人的慾念,與大自然和諧冥合,共生共享,而修練正果,得終極的解脫。
時下流行的政治術語要算是“和諧社會”了。但是,提出要社會和諧的人似乎是缺乏基本的認識。要人類社會得到和諧,首先是人與天地萬物及大自然環境取得和諧協調。越是不斷地向大自然環境施暴,拼命去掠奪地球可再生及不可再生的資源,讓大自然失控,水土流失,悲劇猶生,那裡可能有和諧的社會。
以中國的煤礦開採為例,礦主及有權勢的人為著取得豐厚的利潤,進一步去開發資源,要礦工挖掘更多、更深及更長的礦坑,逼他們越走越遠,危險性必然會更大,意外及人間悲劇頻仍,這源出於人的貪念與慾望,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嗎!這個教訓令人們得到覺醒沒有?正如不丹的內政部長說﹕物質的福祉並不能確保人類彼此相處和諧,也不能確保人類與環境間的和諧。這不是對只知圖利的當權者、追求物慾主義的為政者,當頭棒喝嗎?須知經濟成長並不是人類幸福的唯一途徑。
修馬克在《小即是美》(又譯作《美麗的小世界》)這本書談及經濟發展要兼顧人性與未來世代的生存福祉,從而建立“可持續的發展”,而這種“可持續的發展”的指標是包括精神健康、國民公德、公園普及度、交通、罪犯、污染、回收等。這不就是一個理想的天地人合一、互相包容的社會嗎?要達至這個境地,必然要敬天、澤物、愛人、律己、嚴身了。對資源的揮霍,對大自然肆虐,必然會導至人與人之間的暴力,人類會自食其果。不要以為佛教只談來世,在輪回的說法下,若不重視今生,又怎會有來世呢?唯有善待宇宙天地萬物,才會得到永生。
佛教提出知足者常樂,不知足者萬事憂,唯有壓止人的物慾滿足,就是快樂的源泉。人要肩負起因追求物質滿足的重擔,終日奔波勞碌,連與家人一起共享天倫的時間也沒有,那會有快樂。社會和諧是建基於人與大自然生態環境萬物的和諧,才有真正持久的快樂。
淨心才能淨土,正身才能正人,敬天才能愛民。若是以鬥天、鬥地及人鬥人為立國理念,而全無良知、悟性,這不會是國民的福祉,要構建和諧社會、人間淨土,更加是顯得渺茫無期了。
2005/12/9

不丹第四代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與他的四姊妹妻子
在 6 年前,曾在一個專業論壇,貼出這篇雜文,隨即便惹來爭議,說這個不丹小國孤君並不“寡”,一人共擁四個姊妹為妻,他的快樂子數當然是高。現在,這第四代國王已讓出權力給下代,在此時重拾這個話題,應該是較為適當的時候了。
人間淨土 (上)
回望二十一世紀首五年,人類賴以為生的地球村,究竟還有沒有一片人間淨土呢?
在上一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嬉皮士文化流行的期間,尼泊爾加德滿都曾經一度成為人間樂土,山區簡單純樸的生活,潔淨的大自然環境,社會和諧,沒有戰爭及暴力,是天堂般的美麗。現在,那裡“毛派”紅潮泛濫,進行城市游擊戰爭,令遊人卻步。今年,印度尼西亞巴厘島這個景色怡人的天堂,極端份子多次的人肉炸彈,亦把這個世外桃園變成是人間地獄了。
現今世界亂作一團。美國海灣風災,政治醜聞層層暴露,油價高企,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東聖戰自殺炸彈,西班牙火車、英國地鐵爆炸,中國礦災、水災、毒河,伊朗、北朝鮮核子牙,巴基斯坦地震,愛滋病,禽流感,就好像是一堵末世的場景,差一點便要把世界回復到洪荒的始源。人類的災劫是否應驗了聖經啟示錄中的預言呢?
有學者說﹕人類的進步與文明是源出於”貪慾”,這是否真確,還有待尋找更多例證。不過,人永無休止的慾念,已從其本身的生活表現中顯露無遺了。
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認識到”大即是好”這個概念。美國人住的房子要大,不但如此,前後園也要大,連冰箱、洗衣機亦然。衣服要穿大碼,喝的是特大裝,買車子要加長的大型號,這種觀念已深入人心,一切求大、求多、求快就是好,每天廣告亦是宣傳這一套,故此,人的慾望也是無限地膨漲。這種概念亦成了掠奪的根源。既然本國資源已無法去滿足這種日益高漲的慾望時,便要向外進行更凶狠、更殘暴的侵略了。人慾在無規範、無壓抑的情況下,便回復到獸性的本能上了,以強權代替公理,這是人類歷史文明的進步還是倒退呢?以有限的資源去滿足人類無限的慾望,動亂由此而生。
針對伴隨著人慾橫流而來的社會罪惡,國與國的衝突,民族間矛盾,人與人的紛爭,大自然失去平衡,生態失調,環境被破壞,資源殆盡的問題,三十多年前,德裔英國經濟學家修馬克所提出的“小即是美”的“佛教經濟學”,開始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第一次認識到有這個學說,是在網上看香港電台由李怡主持的一分鐘讀書節目。李怡是前七十年代雜誌主編,一連三期介紹了喜馬拉亞山麓不丹王國“小國寡民”的經驗。這個佛教小國人口只有八十萬,面積是四萬七千平方公里。論國民總收益GDA是全球最低之一,但國民平均壽命在1984至1998年間則增加了19年,這大概是與佛教提倡的“清心寡慾”有關吧。


大熱水一沖,倦意全消。男界是俯前而坐,女界是仰後而躺,一點不苟且。再用一次肥皂擦一擦,圓形膠刷子,在頭皮轉了幾圈,過水後,用乾毛巾在頭髮上猛擦,天旋地轉。若此時不是接過乾毛巾擦臉,眼晴是無法睜得開的。
坐在吹髮椅子上,再三送來香煙,不是有非凡的定力,差點就接受了軟性的誘惑。馬達聲一響,頭上吹來暖風,髮根已乾了大半截。髮乳或髮蠟任君選擇,接著是個火辣辣的場面,灼熱的風,用毛巾輕輕一壓,一個甘乃迪式的花旗裝,就展現在鏡前。
再過三、五年,這個洗頭的小夥子,便會在堂前剪髮,指甲也不用留長,洗頭吹髮的工作,就可以不幹了。用心地替客人整理一番,再用長豬鬃毛刷掃兩掃,便隨即送客到櫃台。在銀盤放下20元,加5元小費,再在洗頭小工手上,按下兩元,連聲道謝。推開玻璃門後,見沒有名車等候,便問要不要召來的士。

想這貴賓式的款待,是唯香港獨有,在這裡,那會有這樣週全的服務。在下課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空檔。女理髮師有點像年青時的陳沖,就叫她做小花好了。言談之間,小花說技術已經過關,惟獨是英文筆試不及格。她來自廣西,在成人英文班念書。她說自己的英文不好,要取得專業美容師的執照,是非常困難的。要是有牌照,便可到市中心,拿到較高的工資,可以有個家。於是,駕車到麥迪遜職業技術高中,向認識多年的美容系主任,取一點考試的資料,送給小花。
不是刻意把小花,與三十年前的理髮滋味相比較,她的技術,是絕不比香港上海師傅遜色。可是,在九龍太子道上,那般理髮的貴氣、品味、享受,到了唐人街,就像潔白的肥皂沫一樣,沖進骯髒的溝渠裡去。3/21/2003

身上蓋上潔淨的圍巾,還帶有濃厚的漂白水味。大師傅必然會不合心意,當然會用不同的手法,再重新整理一番。在頸上先圍上雪白的毛巾,放進衫領之下,再在頸上,纏上白式的皺紙條,這樣毛髮便無法鑽進衣服衫履。照舊來一個美式的花旗裝,彼此心領神會。閉上眼晴,是任由師傅宰割的時刻了,根本上不用擔心,在眼晴打開時,會變成是英式陸軍裝。
此時此刻,正好是夢會“梅麗史翠寶”,在那個年代,那個男士對她沒有柏拉圖式的幻想。有時,也會回味一下,香港中樂團石信之神來的演繹。對民主中國的祈盼,對美滿生活的憧憬。這些零碎的暇想,一一在理髮椅上溜過。
經過一番神遊仙旅後,師傅在膊上輕輕一拍,如夢初醒。只見他拿著大圓鏡,在耳後示意,要看看髮腳的高度,是否整齊滿意。在輕輕點過頭,表示可以後,便掛上鏡子,隨手把椅背往後拉下,灼熱的毛巾在臉上一蓋,毛孔立即擴張,然後用圓形豬鬃毛刷子,在臉上塗上一層厚厚的肥皂沫。

說時遲,那時快,師傅就從深深的口袋,拉出一把“張小泉”剃刀來,打開象牙刀蓋,亮出鋒利耀眼的刀光,再在椅後抽出黑墨墨的粗皮條,磨刀霍霍之聲,再一次令毛管無限擴張,只見師傅手起刀落,幾根汗毛就掉在地上。平生與上海人無仇無怨,除去臉上的鬍子,算是人生第四大樂事了。至於梅麗史翠寶呢,早已飛到九宵雲外了。頭額前毛髮、耳側、眉心、臉龐,一一被冷冷的刀鋒刮過,熟練的手法,快而準,一絲不苟,絕不手軟,可謂痛快淋灕。
清涼的毛巾,在臉上輕輕拖了數下,皮膚立即收緊。抹上一層薄薄的花士令,跟著按住手把,椅子向上一抽,便打回原形。眼晴一開,簡直認不出自己的臉容,精神煥然一新。隨手在頸上的圍巾,扣上號碼衣鉗,以辨別是那個師傅理的髮。
下一站就是洗頭了,這多是由理髮學徒接手。坐在洗頭吹髮的內堂,氣味與上海澡堂無異,讓人容易想起在荔枝角道上的“上海浴德池”,父親是那裡的常客。架上放滿客人的私用洗頭水,母親的大名,嚇然就在其中。一般顧客是用店內秘製洗頭用品,是用肥皂尾加水,浸出來的鹼水,混進不同的顏色,加上香味便是。在乾燥的頭皮上,流過一股冰冷的泡沫水,兩手不停在髮根穿插,像傾瀉的水銀,無孔不入。長長的鬼爪,在頭蓋上下抓動,觸及癢處,豈不快哉!

“剪不斷,理還亂。”這是古人對三千煩惱絲的慨嘆,用頭髮去比喻煩惱,是最貼切不過了。而現代人呢,更逃不了每天要理順一頭亂髮之苦。一清早,先要梳理一番,才可開展一天生活作工的程序,不然的話,便覺得很不對勁,有坐立不安的感覺。
移民多年,首先要學會怎樣替孩子剪髮,因為若是有三兩個孩子,這筆開支是很可觀的。但無論技術怎樣到家,亦無法替自己剪的。這樁差事,原來是要勞煩小姨去幹的,但自從她回流香港後,剪髮便成了大問題了。
記得以前香港理髮業的行規,是在“尾牙”開始加價,加到年廿八便要收雙倍價錢。母親必定要家中所有男士,在加價前光顧理髮店,因女界電髮是不加價的。臨出門口前,千叮萬囑,要師傅剪高一點,剪短一點,否則到新十五過後,又要再一次光臨理髮店了。

在唐人街,理髮是屬三大行業之一,僅次於酒樓及唐人伙食鋪。打開華埠商店名冊,光是理髮店就有二、三十家,有越南人開的,亦有福建、廣東及台灣人主理的,有男理髮師,也有女的,唯獨是舊式上海理髮店,則絕無僅有。
回想起,在太子道及窩打老道交界,那家上海理髮專門店,理髮是一種貼身的享受。踏上台階,只見門前紅白藍三色花柱不停轉動,頗有專業氣派。一位身穿白色大襟短衫,黑色西褲,腳履黑皮薄底便鞋的女招待,笑臉迎人,看來十分順眼。接過燙熱的雪白臉巾,那股濃濃的“滴露”清香,直撲鼻來。坐在薄薄的藤椅墊上,毛巾在臉上擦了又擦,頓然覺得疲勞已消減一大半,全身輕鬆多了。
一聲“小食”。婉拒了各式美國濾嘴名煙,跟著接過當天的《華僑日報》,打開教育版,看看大專院校的報導。《南國電影》及《娛樂週刊》,則推在一旁。招呼極為週到,眼中釘著的當然是銀碟上的小費,及對師傅的額外打賞。遇有名貴房車停到店前,只見女待者一個箭步趨前,直衝店外。打開車門,“經理”、“老板”之聲不絕於耳。若是星期六賽馬日,必連忙問當天的“貼士”,誰是馬主,誰是豪客,她比任何人清楚。
只不過是這裡的街坊,既非馬主,也非豪客,竟有這種高規格的接待,實是喜出望外,這皆因母親是常客,是托母親的鴻福。坐了不久,便有首席一級大師傅登場。經過一輪不咸不淡的普通話寒喧後,心知這客人不是同聲同氣的上海人,便開始用上海話,與在旁的同鄉,談黨國家事了。

